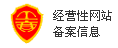在新宪法通过、新政府建立后,反联邦党人并未因对宪法的反对而遭秋后算账。
[51] 参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委赔1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一项行政行为会因不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事由而被撤销或被确认违法,比如事实要件嗣后的变化导致一个行政决定的客观错误。

比如实践中大量存在行政机关违法但无过错的情形,尽管法院往往会正确地判决不构成行政赔偿责任,但这样的判决实际上是缺乏《国家赔偿法》上的法律依据的。既然真正奠定国家赔偿责任基础的是过错,那么继续维持违法归责只能使违法的概念被严重稀释:没有违法的情况下,有时候也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比如前述过错替代违法性要件的情形。[24]在我国,由于采用违法归责,对于违法但无过错的情形,法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是否予以赔偿。比如,在拆除过程中北京丰台城管执法局和南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未能尽到保障现场人员安全的义务,尤其疏忽了对老年人人身安全保护的合理注意义务,对白玉宽左髌骨骨折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对白玉宽倒地受伤承担责任。而在不存在其他加害人的情况下,受害人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当救济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法院也会酌情予以行政赔偿。
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实际上过错要素在司法解释中已经存在。原因就在于,合法的追诉程序、审判程序下尚且不能完全避免冤案的发生,对于不可归责于追诉机关、审判机关的错误羁押、错误裁判,用带有道德可责难性的国家赔偿责任加以评价是不合适的。强调临终医疗方式的选择权,除了尊重病人的主体性地位外,还涉及对不同医疗方式所涉风险的差异化法律规制。
在法律和医疗领域,坚持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对于维护病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又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规定了系统的评估、声明和实施程序,并由自愿协助死亡复核委员会进行监督,持续完善自愿协助死亡的质量和安全性。所谓获得医生帮助权,主要是指对于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病人,有权在适格医生的帮助下,选择适当的临终医疗措施,包括申请医生使用药物立即终止生命,或者在医生协助下实施自杀。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着眼点,不是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而是维护临终病人的生命安全和选择临终医疗方式等权利。
(22)See Lambert and others v.France[2015]ECHR. (23)See Human Rights Committee,General Comment No.36(2018)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24)参见前引(21),刘长秋文,第81页。(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如果并未订立预先医疗指示,则与未成年病人类似,应当由其监护人作出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决定。一些国家早期的法律规定,即便是自杀行为,也属于危及生命安全权的犯罪。对于适用尊严死亡的情形,具体负责医疗适用的医生应当履行报告义务,制作适用情况报告,并附同意尊严死亡的书面医疗意见和有关书面复核意见,及时提交给有关机构审查监督。既然死亡标准逐步法律化,作为对于死亡方式的选择,尊严死亡可以甚或应当纳入法律的范畴。
例如,英国在1961年才从其刑法中废除自杀罪,加拿大则直至1972年才废除其禁止自杀的刑法规定。首先,尊严死亡以保障生命安全为根本前提,如果病人被非法、专断地剥夺生命,就在根本上毫无生命尊严可言。三、尊严死亡的权利构造和体系解析 无论是在国际公约层面还是在国内法律层面,生命权都不是单一性权利,而是体系化的权利集合。尊严死亡事关生命权保障,如果法律对此刻意回避或者语焉不详,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2017年自愿协助死亡法案第9条规定,向医生申请自愿协助死亡的人员必须患有无法救治的疾病,疾病处于恶化之中并将导致死亡,即将在不超过12个月内死亡,无法通过该人可以忍受的方式缓解其遭受的痛苦。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尊严死亡法律制度,也都体现了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的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死亡权概念本身与人权的内涵并不完全契合。在尊严死亡领域,维护生命安全权主要会涉及医生未经病人同意剥夺病人生命的风险。
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尽管尊严死亡主要涉及病人自身的自治权利,但因牵涉医疗措施的适用,所以有必要关注病人获得医生帮助的特殊权利。(32)参见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第85页。反之,主体对生命的自我决定与选择,符合生命权之终极目的在于促进人格发展的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20)也有学者认为,人有要求死亡的自由,为了使这种自由最终获得实现,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只要这种死亡的权利不违背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
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规范尊严死亡的医疗和法律程序,有助于凝聚法律、医疗、伦理等领域的共识,推动构建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理念的尊严死亡法律制度。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3段指出:生命权……保障个体……享有尊严的生命。
如果将人的生命视为一个连续体,那么病人到了临终阶段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理应成为生命尊严的内在要求。对于未成年病人的家长或者监护人代为提出申请的,应当按照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的要求,由医生对申请是否符合尊严死亡的适用条件进行审查评估。
需要指出的是,订立预先医疗指示本身并不等于提出尊严死亡申请,因此,预先医疗指示应当写明准许或者拒绝适用尊严死亡的具体情形。由于尊严死亡与临终医疗措施紧密相关,因此,医生不能无视病人意愿,随意采取临终医疗措施。
(45)在Lambert and others v.France案中,(46)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停止维持生命医疗措施,并不涉及国家保障生命权的消极义务,而仅涉及国家的积极义务,例如此类决定是否具有充分的程序保障、是否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意愿以及是否公平。②早在1985年,荷兰就已制定安乐死的操作规则指导实践。欧洲人权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指出,放弃公约权利的行为,必须通过明确无误的方式(in an unequivocal manner)作出,同时,对(程序)权利的放弃,应当根据权利的重要程度,提供与之相对等的、最低限度的法律保障。该条第3、4款进一步规定,对于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如其对自身利益具有合理认知,在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参与决策过程的前提下,医生可以根据其父母的申请终止生命或协助自杀。
因此,医生责任是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重要维度。我国民法典规定的生命安全,可被理解为防范生命被专断剥夺的危险。
通过审查评估与医疗适用相分离,设置医疗适用环节的最后诊治程序,既能防止尊严死亡的误用风险,也能体现审慎注意义务的内在要求。(36)参见前引⑨,刘召成文,第40页。
不过,涉及尊严死亡的临终医疗方式有不同的类型,包括医生使用药物快速终止生命、医生协助自杀和停止维持生命医疗措施等。首先,尊严死亡应当以病人自主提出申请为前提,不能由医生单方面决定适用。
(40) (二)生命自决权 基于康德哲学,人的尊严关键在于主体自治。(48)如果奉行此种功利主义考虑,将尊严死亡作为安宁疗护资源不足的替代措施,尊严死亡的正当性势必遭到质疑。尽管停止维持生命医疗措施属于尊严死亡的适用形式,但在荷兰和比利时,这种做法被视为常规医疗行为,意味着病人因疾病自然死亡。2020年10月30日,新西兰以65.2%的选民支持率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全国公投,立法程序即将启动。
(13)See Gail Tulloch,Euthanasia-Choice and Death,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2005,p.96. (14)参见前引⑧,王云岭文,第62页。(18)有学者认为,安乐死权就是死亡权,并主张死亡权是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56)在法律上认可预先医疗指示的合法性,对医疗行业具有积极影响。
(21)尽管从死亡权角度分析尊严死亡,看似契合个体的生命自决权,但死亡权概念本身存在正当性疑问,并且难以涵盖尊严死亡领域的医患关系和医生职责等核心问题。对此,关于堕胎措施的法律制度可资参考。